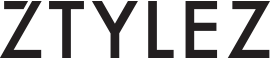每当提到“蛙王”郭孟浩,别人总会称他为:行为艺术第一人、艺坛老顽童、概念艺术先锋,甚或狂人。很多人以为他凭借一身奇装异服才在艺术界打响名堂,然而早在七十年代,在保守的社会氛围下,他早以各种破格的实验艺术进行创作。抵着一直以来别人对他的不理解与轻视,蛙王坚持剑走偏锋,以身体作传播媒介,选用不同类型的媒材打造各种实验、雕塑、画作、装置等。一路走来半个世纪,如今他在艺坛的地位早已不容撼动。虽然年届74岁,但他依然以精力充沛的姿态活跃在本地艺术场域。每逢蛙王有份参与的大型博览会,他还是穿着一身“青蛙装”游走于现场,大玩特玩,乐此不疲。一件如此消耗心神的事却持续进行了几十年,到底他还在坚持些什么?
如今蛙王深隐元朗乡郊,却没有因此与外界脱节。他持续创作,以艺术连接社群,甚至连自己的家,都被他的各种装置布置得像个小型博物馆。从村落小径延展家中一阁,每个角落都被「青蛙」图腾占据,宛如一片专属于他的艺术领地。本集《艺城游记》离开城市,跟随蛙王深入由他一手打造的蛙林(Frog Jungle),希望借由一片小小的领地图个一鳞半爪,看看他穷尽一生都在打造一个怎样的理想国度。
访问当天,蛙王一见面便是以全套「青蛙装」示人。八月炎夏,他穿着厚厚的针织手袖、头上顶着假发与帽子、颈和手上穿戴上不同饰物、戴着青蛙眼睛,手执拐杖,缓缓走进我们视野。一整天下来,他带领我们参觀了他的「青蛙博物馆」,又去了他位於牛潭尾的新家及工作室参觀,更即席为我们表演了一场水火交融的大型实验艺术。纵然大汗淋漓,也不曾喊累。他说这么多年都习惯了,眼神与口吻不会骗人,变装后的蛙王其实也乐在其中。为着我们到来而准备的表演,他开心地说:“又可以玩一顿了!”
“我不只是做行为艺术”
天性好动又多「鬼主意」的郭孟浩,自小就不活在成规之下,别人讨厌呱呱作声的青蛙,在他眼中却是无惧别人非议,自得其乐,如像他本人的自我投射。长大后,别人舞会只选一名女生作伴,他却邀请全班女生出席,大家玩得欢乐,他自称自己为「青蛙王子」。后来到了纽约生活,昔日的王子自然升级成王,自此他便以蛙王这身份自居,并在艺术界留下足迹。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蛙王,其实都是从几十年前慢慢进化而成。早在七十年代末,大陆改革开放初期,他已经在北京天安门进行塑料袋装置艺术。当时蛙王这身份还未成形,那次表演已经被纳为中国有记录以来第一项行为艺术活动。
然而对于这开创先河的成就,蛙王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只是客观条件将他的行为归类,并没有太大意义。对他而言,行为艺术就是一种有意念支撑的行为表演,加上无数个实践的体验,自然成了行为艺术。简单而言,有意识与概念的生活,本来就是一个作品。他说:“我在70年代做了很多行为表演,于是别人便说那是行为艺术,但后来我做过很多雕塑、装置、实验,别人却不提,到了2000年后,我的创作依然被定性为行为艺术,我却不喜欢这种叫法。”一直被称作“香港元祖级行为艺术家”,别人听来如此崇高的名誉,在蛙王眼中,却是把他困在一个狭隘的圈子。他笑言希望跟大众澄清这一点,语气中充满着创作者的无奈。当然这并非是想跟行为艺术撇清关系,而是他多年透过不同创作媒介、表现方式、跟观众互动、即兴表演等实践,只是希望别人能留意到种种出位的行为背后,那些千锤百炼的概念与对生活的反思。

在蛙王的作品中,塑料袋、纸张、竹片、空气、水、火等都可以成为创作媒材,甚至他自己的身体也可以成为艺术的载体。这身看似累赘的青蛙装穿了数十年,很多人都以为这种标奇立异的打扮是为了吸引别人注意,蛙王却说:“我不是以奇装异服吸引人。”从始至终,不论蛙王这身份,还是这身打扮,其实都只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他更渴望观者能将焦点放在他的创作之上。
既然不希望别人只将他归类为行为艺术家,那他自己又怎样定性自己的创作?他说:“那是『会呼吸的生命体』。”当生物、死物、食物、人体都在他的加工下被重新赋予活力,在蛙王眼中看来,没有成不了作品的物件,只要你不被常规所限,任何物件都可以是表现艺术的生命体。
艺术要有开拓性,原地踏步是没有意思。
蛙王的创作理念与他本人一样独特,他与我们分享独一无二的创作理论:“我的艺术主张就是『任次元』,意思就是指任何型、任何量、任何媒介、任何意念、任何维度皆可创作艺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没试过的。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别人眼中的废物,在他眼中却是创作的好材料,他总有办法将平平无奇的东西转化,不论是破坏还是加工,物件总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他说:“艺术要有开拓性,不要重复既有,原地踏步没有意思。”蛙王的大型装置看上去好像凌乱不堪,但其实他自有一套章法。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虽然看似杂乱,其实乱中有序,后来他更建立起一套独一无二的「混统美学」概念,意指混乱中见统一的美学,持续做下去,便成了具标志性的风格。

在几十年的创作路上,他不但没有固步自封,而是通过不同的实验和表演开拓不同可能。他的创作非常重视互动,持续多年的「青蛙眼睛计划」依然进行。他邀请不同人戴上青蛙眼睛,然后为他们拍照,他逗趣地说那是「frog you」,只要戴上他的眼镜,就是把那人「青蛙化」。自古以来乌托邦就是理想世界的代名词,如今有蛙王打造的「蛙托邦」,不同国际、身份、年龄的人戴上他绘制的青蛙眼睛,打成一片,个个笑得开怀,无意中重拾都市人失却的单纯快乐。
“纸张是创意的载体,将纸张抛上天,让创意在天空飞翔”
访问当天,我们参观完他的蛙林后,便跟随他前往偏僻的牛潭尾工作室,蛙王特意为我们的到访准备一场即席的表演艺术。水墨一直是他主要的创作媒界,但他从不喜欢正儿八经地用水墨绘画。新工作室外正好有一片空地,让他可以玩玩把戏。以往在博览会或是展览现场虽然亦会玩,但始终碍于安全性问题,无法尽兴,连他自己亦为此次表演感到非常雀跃。

当我们还在思忖他能玩些什么,蛙王已经大肆地将过了胶片的画作抛在地上,那是他在最近一个大型展览中展示的作品之一。他毫不留情地将它们洒在充满砂石的地上,接着往地上铺上多张大纸,随后拿着几瓶墨水肆意泼在纸上,然后着我们一起拿着一叠叠 A4 纸往天空抛掷。满天飞舞的纸回归沾满墨水的地上,表面漫出墨水的痕迹。蛙王拿出水龙往天上喷水,地上的墨被晕开一片,原来纯白洁净的纸张被墨水覆盖。最后他拿出火枪,将刚刚的一切烧成灰烬。
在电光火石的过程中,他接连用一波又一波具冲击力的行动打破我们对创作的想像。后来他解释道,纸张是现代人承载创意的重要载体,我们将这些纸张往天空抛,就是让创意能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最后纸张飘散落地,沾满墨水,就如同他长久以来的创作实践,不论有多放纵任性,多么离经叛道,最后还是回归水墨。在这一连串看似极具破坏性的行为中,其实他在无声地重塑对水墨的构想。当我们抛却束缚,将这些现成物损耗得不成形,才能打破既有界线,获得真正的创作自由。
其实这并非蛙王第一次进行这个表演,但对他来说,这种实验艺术讲究的是临场性,纵然概念相同,但每次的试验都会受人力、环境、材料等因素而有所不同,背后考验的都是灵活变通的思维与意念。最后地上遗留一片狼藉,还得花时间清理,但这场消耗性极大的表演如像他多年以来的创作实践,化简为繁,舍易取难。在他眼中,这种经过精炼的思考而做的表演才是真正他追求的艺术。即使并非每个观者也能从他的表演中领会到些什么,但至少他在每次过程中亦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尽管做自己理想的作品,即使曲高和寡。
创作的价值不能仅以金钱来衡量

蛙王天生性情乖张,不论在学习、创作、生活都自有一套章法,不被世俗规范。若说他在艺术上深受谁人启发,不得不提水墨大师吕寿琨。蛙王自言早已把他当作父亲般看待,就学期间,当老师教授同学用水墨作画,蛙王已经想到要用活鱼蘸墨,将它们放在纸上摆动,形成“身体动能挣扎出来的痕迹”,结果被老师大骂一顿。后来吕寿琨去世,他亦有感自己的艺术在香港不受重视,便抛却在香港的教职,远走纽约发展。在美国一待便是十五年,期间不时拿出老师以前上课的录影带来听,他说:“每次想到他已经离去,便会不期然哭了起来。后来在纽约重温老师以前的一字一句,总觉得给予了我很多营养。”吕寿琨的教导启发他往后都用水墨来创作,而这位水墨大师给予他的不只是水墨上的启蒙,更是对艺术锲而不舍、自成一家的追求。
创作是好,不创作是好。创作从来就都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
Frog King has taken a different path on the ink road, facing doubts for many years, but his perseverance and resilience have finally allowed him to stand firm on the contemporary ink road, becoming an irreplaceable force in the art world.

而时至今天,昔日受人摒弃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都有价有市。蛙王参与过国际间数千个艺术项目,每天不间断地创作,大型博览会、香港美术馆重开、M+ 视觉艺术馆开张等艺坛盛事都会看到他的身影。然而,热爱创作与玩乐的蛙王并没有因为如今的地位而自命不凡。相反,他仍不时走到社区和街坊大玩特玩,更将自己的墨宝、作品随手送给参与者。近半年,他在元朗开展一个「谷亭街之友」的项目,邀请街坊一起戴上青蛙眼镜,更为他们每个人改了一个称号,写成蛙王独有的「画字」再送给他们,彼此玩得不亦乐乎,更被街坊们以「会长」相称。
然而将作品随意派发的行为犹如跟画廊、拍卖行唱反调,我们问这不是让你的艺术路更难走吗?他却淡然地说:“理论上的确是物以稀为贵,将作品卖贵其实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更高的境界就不是说这些。如果在作品中找到一个有内质、富有哲学性的启发,那么创作的价值就不可以单以金钱来衡量。”相较几十年前,大众对他的创作强烈排斥,如今苦熬50多年,能得到别人的理解与支持已是弥足珍贵,在艺术道路上逆行多年,痛并快乐,任何物质与名誉都不可比拟。
“我是一个有承担的无形文化财产的工作者,不只是艺术工作”

作为香港表演艺术第一人,蛙王的出现确实史无前例地开创了概念艺术的生态,然而他本人又如何看待自己在艺术方面的影响呢?他表示:“其实历代发生过这么多精彩事,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我的创作其实都是些很肤浅的东西。”对于自身的艺术表现形式,他更自嘲说:“我就是最老套最笨的那个,弄到全身都是东西,满头大汗还在做,其实是很蠢的做法。但反过来看,却成了最杰出那个,因为我从原始中重新走出来。在香港个个都是正常生活,突然间走出一个疯狂的人,但在艺术层面来说是最独特的。”
他曾笑称自己是“下个世纪的艺术家”,数十年前的创作走到今天才开始被接受,这位艺术先行者或许在心底里都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孤寂。

在纽约打响名堂,甚至被邀请回中国举办展览,直到 1995 年回流,蛙王便不再离开过。他对于本地艺坛的贡献不容置疑,但香港这片土地与当时被视作艺术大都会的纽约相较起来,可以说是从大水塘游回小鱼池。到底香港这个地方能带给他什么,使他甘于驻足在此?
He said, “I received cultural education from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in Hong Kong, which inspired me a lot. My current creation is about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n society, which is actually a way of giving back to society. I believe that by continuing to work slowly, I can pass on my art and culture in society, like planting a fruit tree that will bear fruit someday in the future. In fact, the talents of the new generation also emerge in this way.” For a long time, Frog King’s creations have brought countless joy to everyone, and the reason he continues to create is to fulfill a sense of miss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He believes that what he is doing now is a kin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he is one of the inheritors.
“蛙托邦是一个开心、快乐、理想的未来世界”

He shared with us: “It’s really not easy to do art. It’s not enough to put yourself in a desperate situation and then come back to life. You have to die dozens of times, struggle in great difficulty and hardship, and suddenly stand out after that. Only the works that come out have depth and lasting appeal.” Over the past 50 years, the Frog King has done thousands of projects, putting his all into each one. He said, “As long as you treat it as a daily routine, you won’t feel tired.” Being able to achieve something, even if it’s just attracting a little attention from others, makes him happy.
年过古稀,如今的蛙王不再如年轻时般「跳跳扎」,手执一支拐杖的他即便走得缓慢,但仍不时拿着相机、青蛙眼镜、墨水走进社区,与街坊们玩在一起,邀请他们进入他所打造的「蛙托邦」,他说那是一个开心、快乐、理想的未来世界。当玩得累了,便回归蛙林休息,继续埋首创作。
最后我们问他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艺术家,他想也没想便应道:“快乐的青蛙,能快乐便好了。”他曾笑言仍向着9百万件作品的目标进发。完成一天拍摄,我们陪他从新工作室回到屏山的家,一个月后,这个自成一角的蛙林恐怕就要面目全非,但我们知道他自有无穷的创作力,他对艺术的坚持使“蛙王精神”在每片曾踏足的土地上都留下印证。
蛙林迁址,重点从来不在于地方本身,而是艺术家创造快乐的本能。那个耗尽一生打造的「蛙托邦」不曾消失,如同他的艺术一样,早已深入香港的土壤,种下永恒。
执行制片人:莫克安格斯
制片人:韦维琪
编辑:刘碧莹
摄影:陈安生,李安迪
摄影:陈安生
视频编辑:陈安生,李安迪
设计师:程丹娜
特别鸣谢:蛙王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