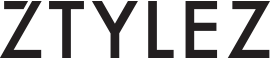他的舞台剧创作总渗透一股魅力,作品不时从经典文学著作中取材,却又以层出不穷的新意颠覆经典,作品意念艰涩,却又令人回味。他是林奕华,香港著名舞台剧导演,从1991年成立「非常林奕华」剧团至今30年,制作超过60套剧场作品。他的作品远超于一场单纯的表演,而是启蒙观众探索自我,反思时代、社群、如何自处的一把钥匙。
如果说创作是一个寂寞的过程,那么生产一套剧场作品或许是一种相对热闹的方式。各个演员忙着奔走于舞台上,配合声响、灯光、道具,身体姿态化作线条,情绪渲染出色彩,让舞台如画布般呈现出一幅充满故事性的图像。然而掌声过后,镁光灯熄灭,那些习惯在阴影中观察的导演又是如何看待每次演出?对林奕华来说,创作舞台剧其实亦是在绘画,表演就是一个移动的画面,而他就是背后挥笔的人。从17岁加入大台担任电视剧编剧,后来到外国深造,成立自己的剧团,他自言自己偏喜欢向难度挑战。舞台剧创作从来并非主流,但对于一座城市中的文化滋养来说,亦是不可或缺。
本集《艺城游记》邀请林奕华导演跟我们聊聊他的剧场创作经验,让我们与他相遇在剧场之外,细听他如何用舞台作品带领观众们跨越空间与时间,迸发更多对艺术与生命的想像。
“我不希望观众在舞台上看到全部,而是让他们看到一部分,想像一部分。”
很多人认为欣赏一部舞台剧就是要看演员的演技,然而对于Edward来说,他却更在意如何打造一个比舞台更大的想像空间,而非单单只是导戏。他说:“电影跟舞台剧最大的区别并不只是在于电影有特写镜头,或者可以快速切换时间,因为舞台剧也能以灯光切换时间,演员走位都是一个镜头的调度,它们的区别在于舞台导演怎样视『时间』为时间,『空间』为空间。”当别人希望舞台焦点落于语言表达,Edward已经超脱于框架本身,希望观众能获得思维上的启发。舞台空间不再是限制,而是能为观众提供一个更广大的想像领域,他说:“我希望观众看到的舞台不只是这样大,而是更大更大。”
基于过往曾参与电视剧、电影、剧场的幕后工作,他笑言自己是个「以拍舞台剧去拍电影的舞台剧导演」。既然曾涉足不同范畴的创作方式,我们都好奇他比较偏好哪种。Edward 表示以前觉得电影制作讲究技术上的合作,而舞台剧则比较轻松,因为大家的焦点都放在演员与观众的距离之上。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创作舞台剧亦要处理灯光、舞台设计等问题,导演不能只考虑如何去导戏,而是通过舞台的整体呈现,为观众提供一个最佳的看戏视觉,甚至要让他们从多感官地去看,逐渐觉得两种方式的分野其实也并不大。
然而,Edward 深知观众在这短短一两个小时的视觉叙事中,肯定接收不了所有制作上的信息,但只要当下观众坐在台下专注于演员的表演,那些瞬间已经是完美。可能他也回答不了自己更喜欢哪种表达方式,因为那都是一种形式上的追求,希望观者通过作品获得共鸣、认识自己,才是他看重的事。

“我的过往作品都有一个核心的主题,那就是成长。”
Edward的作品既有改编经典著作,亦有不少关注城市现代生活、人际关系等广泛题材,然而不论作品跨越古今,回溯本源,都是跟「成长」有关。人一生总会遇上很多难题,而我们都是在碰壁、重新认知、改变等这些阶段中,慢慢蜕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他跟我们分享自己最喜欢到学校跟学生接触,因为他们不容易被既有的思维捆绑,而在交流的过程中,总会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启发。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导演,他表示不能让学生们有感自己很有权威,唯有冲破身份上的界线,跟他们打成一遍,思想上才能真正互通。正因为他自身就是一个注重双方交流、对着别人总是流露着好奇与关怀的人,才使他在观察与沟通中,积累种种创作灵感。
但灵感并非去寻找就有,Edward 认为创作者要先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己的不足在哪,对别人有同理心,才能分别出哪些能成为创作的灵感与养分。他笑言自己仍要继续成长,而这种面对对方的直接沟通,更让彼此能认清自己,或是在别人身上学到一些自己缺乏的本质。

“我最希望观众能在作品中看到自己。”
回顾过去的创作,其中不少是改编自经典的著作,从《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水浒传》《西游记》《包法利夫人》等,不同题材的作品都能被Edward改编成舞台剧。将这些经典故事以剧场形式表现出来,到底其中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他说:“从文本到空间,最困难就是让作品跟你对话,学会如何跟作品聊天是我过去最大的收获。”他的创作从来不在于重塑经典,而是从经典中抽取其中的思想内核,并将这些想法延伸至当下。他说:“这些文本都有内外部分,外是指当时的社会及时代,内是指情感,当你明白情感以后,便不容易被那种壁垒分明的厚墙阻挡了你去连接文本。”因此他可以拿《聊斋》跟外国电影《婚姻故事》作比较,无关中西,无关时代,某些情感与人伦关系都是世代相通的。

Edward经常在作品中挑战时间、空间、性别的表现方式,就如刚于9月在西九自由空间公演的《寶玉,你好》,剧中两名演员隔空共演,而观众亦可自由流动于剧场空间,颠覆了传统的表演模式与观看经验。面对如此破格的表演方式,未见得人人都能意会作品的巧思与深意,对于剧场创作人来说,观众能否看懂剧目的讯息都是恒久的命题,究竟他们最关注自己的作品能为别人带来什么影响呢?
He said, “In fact, it’s all about emotions. I hope the audience sees themselves, meaning that I hope they will have more reservations about themselves before entering the theater, so they will have more conversations with themselves in the following time.” He feels that although the audience may not admit it, deep down everyone desires to see themselves in the performance. He continued, “The surface layer is identification. Popular plays generally show the audience their ideal selves, making them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The second layer is when the audience sees their own problems and begins to reflect. The third layer is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s, accepting their flawed selves, and starting to seek change without demanding answers or validation from others.” Providing the audienc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rediscover themselves in a work is truly valuable.

每个人的生命有限,但创作可以让他由一个信念去另一个信念,一个生命去另一个生命。
剧场表演让空间能延伸至无限,其实信念亦然。或许正因抱着对现时的不满足与对未来的期盼,才使 Edward 通过创作去发掘更多可能。他认为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经历是艺术家极大的创作土壤,当我们面对生活中各种失望、痛苦、寂寞的情绪,才会建构出对美好的想像,于是才有创作产生。他觉得若生活未曾遭遇过辜负,遇到的都是美好的事,那那些人未必能成为有趣的艺术家。每个人生活中总是弥漫着爱与疼痛,我们都通过艺术来补洞,唯有丰美与荒凉互相交织,人生才是完整。

Edward还跟我们分享了一套「单恋生命」的独特理论,就是对万物都要怀着期待与仰慕,并且永远相信有一片高于自己的天空。他引用王尔德的一句:“我们都在阴沟里,但永远仰望着星空。”Edward 说这三十年的创作都受不同艺术家影响,即使他们的作品已是久远的产物,但其中承载着的想法与信念不会随时间老去,如今他的舞台创作其实亦是承接了那些意念。
「舞台是我的家、火車站,我猜它亦會是我的墳墓。」
从 1991 年创立「非常林奕华」剧团至今,累积已有 64 套剧场作品,Edward 这几十年来的生活都与舞台息息相关,除了是依靠,舞台早已是他生命的归属。
He said, “We often have misconceptions about death, there is a great anxiety about the end point, feeling that everything ends at that end point, but the value of crea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does not impose limits as limits, and endings are endings. Just like Van Gogh has been gone for a long time, but when we see a certain shade of blue, we still think of him.” Because of creation, death is no longer frightening, because life continues forever through the works left behind. 他说:“我们经常对死亡充满迷思,对于终点有个很大的焦虑,觉得所有事都完结在那个终点,但创作的价值正正在于他不会令到限制是限制,完结是完结。正如梵高离去很久,但当我们看到某一种蓝时,仍然会想起他。”因为有了创作,所以死亡不再可怕,因为生命都通过遗留下来的作品永远延续。
回溯过去数十年的舞台经验,他说:“作品就是一个人由出生到他离去前留下痕迹的地方,如果我没有参与剧场的话,如今我留下来的痕迹未必是现在这些。最近因为剧团 30 周年,我拆开这些作品重看,其实是激动的。我发现他们都可以连成一线,连出来的就是一个地图,而这个地图就是香港。”

曾经到外地发展,作品也曾在不同地方上演,最终选择在这片孕育他的土地上创建剧团,默默坚守数十年,背后是否全然是爱?这座城市又给予了他什么创作养分?
Edward认为香港给予他的能力并不单一,除了语言上的学习,亦有不同文化启发,而更重要的是在舞台创作上的机遇。如果当初选择在别的地方发展,如今可能不会做到这30年的份量。但他亦坦言对这个城市「既爱又恨」,回想自己17岁进入当时的大台当编剧,18岁签约,19岁便离开,从此便结束了短暂的电视生涯,因为当时的他已经发现自己并不喜欢那些大众化的东西。自90年代从英国回来香港发展,他发现香港早已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社会被物质、八卦娱乐、单向式教育等填满,他始终无法舒坦地接受社会上形形式式的糜烂。他说:“我这30年来都在做这件事,就是不被大众肯定的价值观框住,而是去明白它们与自己的关系,然后再作出选择。”但他何尝不明白在主流中逆行的难处,他感叹道:“所以注定你在这里不会很受欢迎,因为你无法拥抱这些价值观。”

这些年来,“非常林奕华”剧团与跨媒体、不同城市的艺术家及团体合作,以开拓性的视野创写了华语戏剧的新面向,纵然文艺从来不是社会的主流,但这64部作品无容置疑地为文化界带来了广大的影响力。导演本身又如何看待这阶段的剧团?
He said, “Too few people have seen it, too few people have seen these 60 or so works. This may not be a fact that I can change within my abilities, becaus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roup to now, I have made more than 60 works. If someone is willing to watch them all, you can imagine that a lot has happened in them. They are all related to myself, to this place, and they record how much I feel about this place. But whether these events are meaningful to anyone, whether they are meaningful for the future, is not something I can decide. I can only be grateful that they have all happened, and that th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can be related to the times and people’s hearts. I feel that this is already a gift to myself and to others in my life.” Regardless of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being able to create works that touch people’s hearts is the greatest gift to the creator.
感谢「非常林奕华」这些年来为我们呈献过的剧场,让我们能暂借一场戏的时间,与创作人相遇在舞台,跨越空间与时间,落下对生命更多想像。倘若没有这六十多部作品的出现,如今的文艺界也未必是现在的模样,但凡出现过的,都必留下痕迹。愿剧团未来还有更多30年,让导演继续用舞台刻凿成长,让每次相遇都练就成不解的缘份。
执行制片人:莫克安格斯
制片人:韦维琪
编辑:刘碧玉
摄影:李安迪,朱健尼
摄影:李安迪,朱健尼
视频编辑:李安迪
设计师:陈爱德
特别鸣谢:林爱德;香港艺术中心场地租赁